
左还是右:秦晖讲座再思考
作者:映光
秦晖教授线上讲座的最后一个环节是点评和讨论,赵晓老师和王干城老师分别作了发言。
赵老师提了一个问题,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纵论了万历年间,张居正的失败,成为中国命运交叉的十字路口,唐德刚提出历史三峡论,谈到了中国的转型期是个瓶颈。
我们正处于一个“至暗时刻”,可否突破历史。
王干城老师则对秦教授的“历史偶然论”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决定英国从大宪章到光荣革命取得成功的决定因素是信仰。这就像安装上了人工智能系统的精确制导武器,即使在某一时期出现了偏差,但却总是指向一个原本设定的目标。
他并举例说,英国的现代化与首个提出“三民主张”的威克里夫密不可分,而他对《圣经》的翻译,是推动英国转化的那个“精确制导”因素。
秦教授回应,他面对如今这样一个至暗时刻,也很悲观。但回望历史,这样的至暗时刻并不少见,例如20世纪中叶,茨维格面对斯大林的极左和希特勒的极右,便曾对民权社会感到深度绝望,但历史往往并未按照一种大概率的趋势行进。
秦教授说,他并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因为,唯物论不但无法解释人文历史,连自然世界也解释不了。无机物变为有机物,进而变为蛋白质,产生高等生命这件事,就是一件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他虽然并不是一个基督徒,但他却相信,主宰这一切的是一种“冥冥中不可知的力量”。而他把“至暗时刻”的希望,寄托在“冥冥中的那种力量”中。
但秦教授并不完全赞同王干城老师的观点。他认为威克里夫是一位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是空想社会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并不是一个“三民主义”的代表人物。
此外,他不否认,新教对推动资本主义和现代政体有帮助,但这些事情并不是只发生在英国,同样的国家却没有改变。
秦教授认为,基督教并不是只对推动民主政体有作用,也与左派思潮相契合。马克思便对威克里夫有很高评价,因为,基督教有均贫富的社会主义理念。
时间关系,秦晖教授与王干城老师的辩论并未展开,但却引发了我的很多思考。
我在青年时代,信仰基督前,如果非要贴一个左或右的标签,基本上在新左派和自由派之间摇摆。思想偏“白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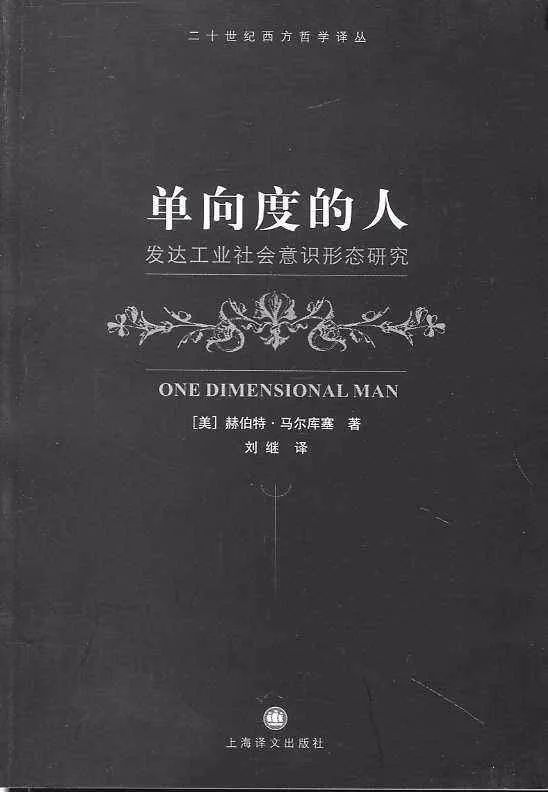
大学时代,喜欢读马尔库塞和法兰克福学派的书:《理想和革命》《爱欲与文明》《单相度的人》,深受影响。新左派反对斯大林式的专制主义,提倡民权,但同时拒斥自由主义。
我喜欢听摇滚乐,憧憬那个充满革命理想主义和嬉皮精神的西方六十年代。
随年龄渐长,我逐渐喜爱萨特、加缪、德里达、罗兰·巴特和巴赫金的存在主义和后现代解构主义哲学思想。
相信没有绝对真理,没有终结理想,语言只是符号,可以随意阐释。
这也令我一度重新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兴趣,读老庄,修禅宗,认识虚无。
这个时期,英国愤怒青年和美国垮掉一代文学对我的影响也很大,这些作品对欧美社会的深层批判,让我感到绝望。中国变革的标杆,不过也是糟粕。
约翰·厄普代克的小说,是最为真实的绝望的美国中产社会。《搏击俱乐部》《V字仇杀令》《猜火车》和《小丑》这样的电影,则是美国和欧洲骚乱的思想根源。
信主后,我像飘摇的水草,找到了命定的锚,寻找到彼岸世界,和生命的光芒。但我仍不喜爱给此岸世界的很多事物,贴上简单的标签。
我喜爱听秦晖教授的历史课,也会看齐泽克宣讲马克思,我会听德里达的徒弟斯蒂格勒谈未来哲学,也会看大卫·鲍森讲《启示录》。不过,我终归会回到《圣经》,并转变成一个保守主义者。
新京报创刊时,我所在的文化副刊部曾开创了一个“个人史”栏目,我在其下设立了一个寻找80年代专题,采访了“今天杂志”“星星美展”“四月影会”等专题。这个栏目以采访一个人的口述历史为主题,其实更偏重思想史。
一个知识分子的历史,最重要的不是他经历过什么事情,而是他思想演变的过程。
近代思想史,左右之争,一直是主旋律,主要矛盾。但孰为左右呢?
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左派,基本上是西方的极左派,而中国的右派,则是西方的左派,即自由派或新左派。
西方的右派是保守主义,即保守基督信仰原则的一派。因为,耶稣在上帝的右边,即right,正确的,而左是left,是离开,即离开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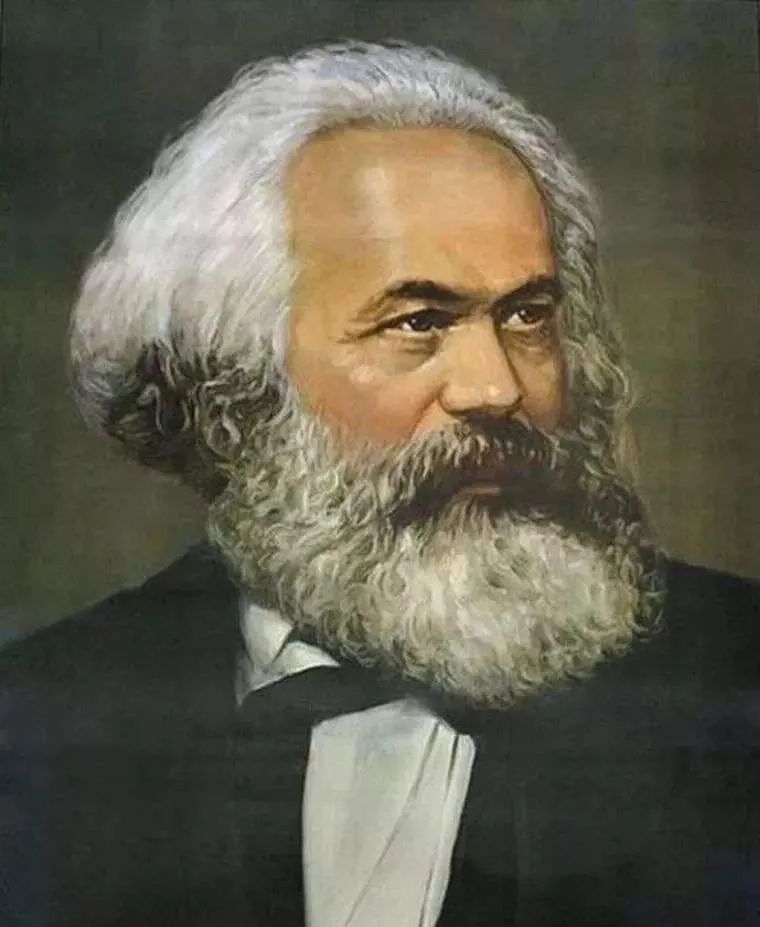
有趣的是,影响二十世纪的两个无神论思想家,马克思和尼采,分别是极左极右两大思潮的开创者,却都有着极强的宗教背景。马克思生于犹太拉比家族,其思想中,有很多内容与犹太教相似。曾赴以色列参观过“共产主义”农庄基布茨,其实跟马克思主义没有任何关系,其均贫富的观念,主要来自犹太教思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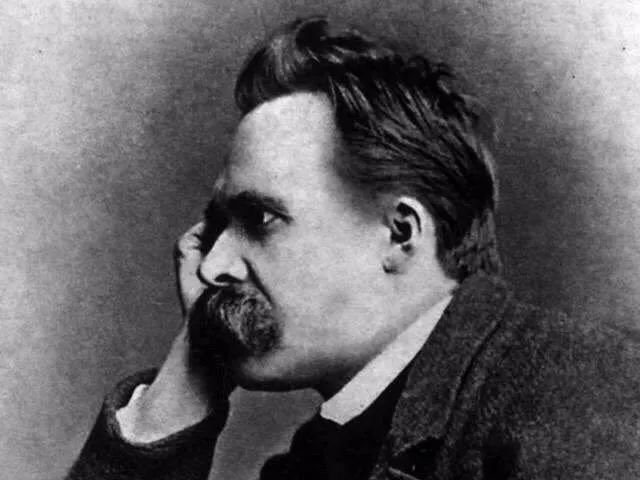
尼采的父亲则是一位虔诚的牧师。这反而成为尼采坚决摒弃上帝,离经叛道的主要原因之一。
托尔斯泰的《忏悔录》开篇即回顾其青年时代,对腐败而虚伪的东正教的厌恶,是他背弃基督信仰过上桀骜不驯地堕落生活的主要原因,直到晚年,他才重新回归信仰,厘清信仰和宗教的关系。
无独有偶,林语堂在他的回忆录中,也提及牧师家庭,令他年轻时对宗教,反而特别反感。
马克思主义成就了斯大林样本,而尼采超人哲学则成就了希特勒样本,尽管,也可以辩称,这些独裁者脱离了他们原本的思想。
德国战败后,尽管对极右翼法西斯主义有深刻反思,但仍旧是西方左派思想的温床,法兰克福学派新左派即诞生于德国。德国总理默克尔所在政党称基督教民主联盟党本是一个保守主义政党,但其“姊妹党”基督教社会联盟党却是一个试图将基督教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想相结合的政党,党部挂有基督像,也挂着马克思像,默克尔推行的左派执政理念,即源于此。
秦晖教授说,拥有自由环境的美国其实一直是空想社会主义的温床,也有很多人勇于实践,建立基布茨一类的社会实验样本。但只要这种实践是基于自觉自愿原则的,就不会对社会造成任何伤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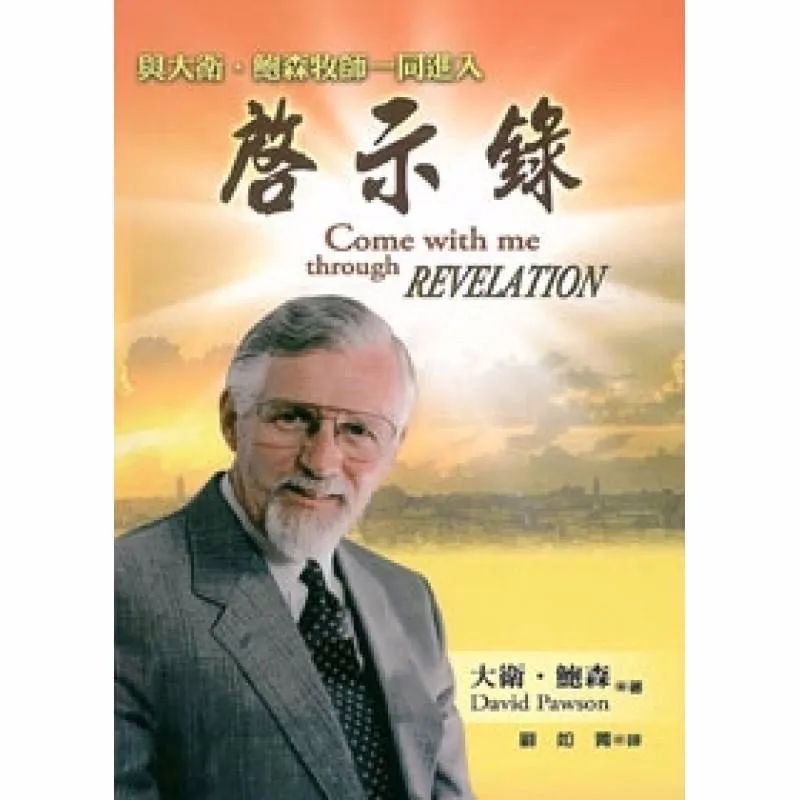
大卫鲍森在启示录中讲道,基督耶稣再来时,会在地上坐王一千年,他所施行的一定不是民主制,而是君主制。他要示范给人们看,他是如何治理社会的。但即使耶稣坐王,仍无法完全翦除人性之恶,仍会有人拜在撒旦名下,反对祂。所以这一千年后,撒旦要重新得到释放,上帝要重新行驶审判。这难道预示着,即使耶稣坐王,面对人性之恶,也将以失败告终吗?当然,故事的终局,上帝会把撒旦打入永火,因信称义者重获永生。
大卫·鲍森是想说明,制度并不是实现乌托邦的钥匙,左与右,并不是终极答案。这段解读非常深刻。
抛开左与右的思想之争,秦晖老师表示,神学家不是冲过历史三峡的那艘船,神学家没有行动,付诸行动者,为圣徒。
自由是人性中都渴望的,每个人都知道自由是好东西,但人又是自私的,一方面是想要坐享其成,一方面又想获得比别人更多的自由。为公众争取自由,还自愿舍弃比别人获得更多自由的权利,这便是圣徒。
圣徒是极少数人,圣徒改变历史,也是小概率事件。若非彼岸世界在召唤,也就没有具有自我牺牲精神的圣徒。




